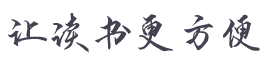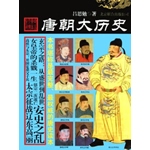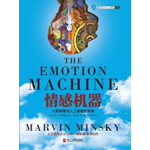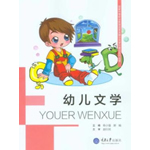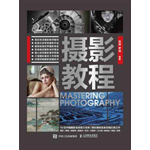图书详情
内容简介:
当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就印象比较深刻地知道,虽然鲸鱼外观像鱼,但并不是鱼。今天,这些分类问题已很少让我激动了;当有人断然告诉我,历史不是科学时,我也不会过分忧伤。这种术语问题是英语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在欧洲其他诸种语言中,与“科学”同义的词是肯定包括历史这个词语的。但是在英语的世界里,这一问题的背后还有很长的历史,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正是一份可以做关于历史方法问题的简明导论。到18世纪末,当科学已为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关于人类自己身体特征的知识做出了极大贡献时,人们开始询问科学是不是也可以促进人类关于社会的知识。社会科学的概念,尤其是这其中历史的概念是在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自然界所使用的方法被用来研究人类事务。19世纪上半期,盛行的是牛顿的传统。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机械装置;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1年出版《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人们至今仍旧记得这部作品的名称。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伯特兰・罗素后来回忆有一个时期,他希望早晚会有“一种像机械数学一样的人类行为数学”。1那时,达尔文引发了另一次革命;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那里得到启示,开始把社会当作是一个有机组织。但是,达尔文革命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完善了莱尔①在地质学中已经开始的研究――把历史带入科学领域。科学所涉及的不再是一种静止的、与时间无关的东西,2而是涉及变化、发展的进程。科学上的进化观念确定了、完备了历史中的进步观念。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在第一讲中所描述过的史学方法中的归纳观点:首先收集事实,然后解释事实。毫无疑问,可以想象出这也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很明显,伯瑞(Bury)也有这种想法,他在1903年1月的就职演说作结语时,把历史描述为“一种科学,一种不折不扣的科学”。伯瑞就职演说后的五十年见证了一股强硬的反对这种历史观的潮流。这期间的柯林武德,他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急切地想在科学探究的对象自然世界与历史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来;这期间,人们很少引用伯瑞的格言,只在嘲弄时是例外。但是,这时的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是:科学本身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使得伯瑞的观念似乎比我们曾想象的要正确得多,尽管正确的理由是错误的。莱尔对地质学带来的影响,达尔文对生物学带来的影响,现在又轮到天文学有这种影响了,天文学已经变为一门研究宇宙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科学了;现代物理学家经常告诉我们,他们研究的不是事实,而是事件。